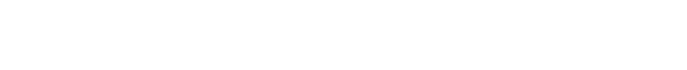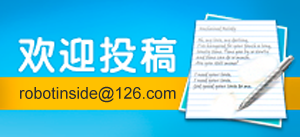早在2011年,鴻海的郭臺銘就拋出了“三年內百萬機器人換人的誓言。從各方面的信息來看,郭總似乎沒有完成當初的計劃,但有報道說,因為自動化升級,富士康昆山工廠已經辭退了超過一半的員工。一個關于“機器人換人”的最新消息是,外交部王毅部長為科大訊飛的智能語音產品點贊,希望外交部能引進這項語音識別和智能翻譯技術。這兩件事都在告訴我們,機器人真地來了,那么職業教育該怎么辦?
按照一般的思路,職業教育所能做的無非是調整專業結構、提升培養層次、提高培養質量。但長期以來,這些工作都是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核心議題,長期努力并沒有使職業教育達到理想的服務能力,這暗示,職業教育的問題不出在具體策略上,而在于基本哲學上。
到目前為止,職業教育領域的大多數改革都基于“對接”哲學:職業教育應該與產業進步、企業發展對接。在我看來,應該區分宏觀勞動經濟學與微觀勞動經濟學。國家和教育部所提出的“對接”應該被視為宏觀勞動經濟學的范疇,是對整個職業教育事業的宏觀指導,但具體到某一學校、某一專業、某一項目則不盡然。在宏觀上,如果職業教育不與產業、行業對接,將造成人才培養的極大浪費;但在微觀上,相比學校人才培養量,社會的用人需求是龐大的、海量的,至少在理論上,所有專業的所有畢業生都有可能對口找到工作。所謂的就業困難,只不過由工作環境、工作薪酬、發展前途等因素所造成,與專業設置等教育因素關系并不十分緊密。
由此,有理由認為,謀劃面向未來的職業教育時,應該跳出“對接”的思路,在更為前瞻的立場上規劃職業教育發展。所謂的“不對接”,大致有以下三點。
1. 不對接產業。筆者第一次在淘寶上網購是在2005年的上海,自己在網上下單然后就有人送貨上門,真地覺得非常神奇。然后就發現,快遞產業在中國大地上迅速膨脹。那么,10年前有多少人預計到了今天快遞產業的規模和人才需求?誰能想到,網購相關產業需要大量的超級計算方面的工程師、網絡工程師、物流工程方面的工程師?對接產業在今天這個變化速度極快的世界就意味著落后,就意味著被淘汰。不對接產業,則可以使自己站得更高,以更加超然的態度對待產業變遷。
2. 不對接職業或崗位。從德國傳進中國的課程改革理念的邏輯大致都是:職業教育是為職業服務的,所以要把企業的崗位需求作為教育活動的起點,因此,要對崗位能力進行深入分析,然后將其映射到學校的教學環境中。這套東西中國人很受用,但奇怪的是,并不是所有國家都認同這種想法。比如,美國人就不大認可這套東西,為什么?我的解釋是:德國人的這套教育理念與體制與其傳統工業國的地位是相稱的,傳統工業是馬克思批判的異化的工業,是以機器為中心的工業,所以相當穩定;而美國相比德國是一個新的工業國,新技術、新業態出現地更為頻繁,新工作、新崗位層出不窮,學校今天對接的崗位到了明天可能就過時了,所以,美國人寧愿搞綜合高中的職業教育,也不愿意學習德國人早期分流的方式。中國呢?在這個星球上,與美國最像的經濟體可能就是中國了,網購、移動支付、BAT等就說明,中國的職業世界變化可能已經是世界上最快的了,所以,對接職業或崗位開展職業教育的想法從根子上就是不合時宜的。

3. 不對接生產過程。在所有的“對接”口號中,“教育過程對接生產過程”可能是最荒謬的,到書店里找企業管理的書,“流程再造”方面的書籍相當地多,企業都在不斷地再造生產與管理流程,教育過程如何與之對接?許多地方在招商引資時對富士康承諾了職業院校的配套,但在“三百萬機器人”計劃面前,學校的電子相關專業如何對接這樣的生產過程?從福特時代開始,在真實的生產過程中,尤其是工業生產中,工作就已經被高度分工、高度碎片化了,每個工人只負責極小范圍內的簡單工作,技能被極簡化。這樣高度分工的生產過程對工作中人的能力需求做到了最小化,真地對接了這樣的生產過程,學校大約60%的教育活動都可以取消掉了。但對接口號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這個口號的鼓勵下,許多學校開始引進企業的真實生產設備,甚至追求學校的實訓設備比企業的生產設備更加先進,造成的浪費難以估計。
上述的三個“不對接”其實并不新鮮,許多職業教育工作者早已認識到工作世界的變化速度遠超職業教育的感知與反應能力這一事實,職業教育以追趕的姿態迎接這一挑戰時只能是被越拋越遠,所以,提出回歸基礎知識、基礎能力,回歸人文素質教育的主張。但很明顯的是,這樣一來,職業教育與工作世界聯系緊密的基本特征就被削平了,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存在的必要性也就被削弱了。我相信,三個“不對接”的本質是職業教育應該“適當超越”——超越當前當前的生產過程、超越當前的崗位需求、超越當前的產業結構。可是“適當超越”真的可能嗎?